困在系统里的人开始持码上岗

上海在今年(2025)4月开始推行外卖快递骑手"交通安全码"(下称交安码)等系列措施,将骑手个体分级为"绿、黄、红”三色安全等级,并要求平台企业将该标识直接与骑手从业资格关联。观察社媒,不少人反映,此做法令人联想起新冠封控时期的"健康码",质疑措施必要性和具体成效。
不过,措施对一线骑手的影响,远不只一种一刀切管理的"创伤记忆"重现:以交安码为代表,上海近年推行一系列管理骑手群体的交通安全措施,试图介入外卖快递平台的劳工管理模式,也在过程中达成了更深入的劳动控制。
数据上的交安情况改善,实际上并不来自解决源头问题,而是进一步压迫骑手群体的”恶果”,令一线骑手陷入失声、失权境地。

交安码,联合的制裁?
7月3日,上海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媒体说明了交安码的推行细则(1):
上海针对快递外卖骑手群体推出交安码制度。依托新建的数据系统,政府以绿黄红三色标识骑手安全等级,要求企业将骑手个人交安码颜色直接关联其从业资格,并以骑手交安码统计信息进行企业、站点的评定。
|
红标🔴 |
当月累计2起或以上有责交通事故、存在未处理的一般程序有责交通事故,或存在4起或以上未处理交通违规 |
|
黄标🟡 |
当月累计5起或以上交通违规、存在未处理的简易程序有责交通事故,或存在未处理交通违规(即1至3起) |
|
绿标🟢 |
当月完全没有未处理事故及违规,且累计发生的事故及违规量不超过红、黄标规定者 |
Source: 《上海市同城配送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自律公约》(下称《自律公约》),不合规使用号牌或车辆的情况外的交安码变换规则
交管部门表示,交安码意在推动“企业监管 + 平台约束 + 骑手自律”的安全治理模式,促进平台企业以此改变原有管理模式。
同时,交安码并非孤立存在。政府要求平台企业将骑手相关数据接入新建的“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”,结合针对骑手群体车辆的专用电子号牌,以监控、算法与评分,监测各平台下骑手的违反交规行为。

至此,一种新的监管模式浮现:交管部门通过交安码等措施,试图加入并与平台共同管理骑手。透过设立交安码相关入行门槛、要求数据共享、进行交安评分及通报等,政府能够重新掌握平台企业的权力边界,"促进行业健康发展"。
然而,以加入监管而非修正现况为动机的交安码,与平台管理共同形成了更大的压迫。新模式反而延续了平台漠视骑手安全与意见的管理逻辑,没有实质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,更加正当化了平台和骑手间的权力不对等。
上路骑手没有变安全
交安码推行后,好转的交安数据,能证明骑手的工作安全有提升吗?结论并不明确。
理论上,交安码的规则确实在引导更安全的驾驶,推行后的整体事故量也确实下降,比如据上述报道,上海今年涉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下降了14.8%。但究其本质,骑手的"老板"依旧是平台,加上交安码的平台规则,实际依然允许,甚至鼓励骑手的不合理赶单。
事故量的下降,更可能是被停止接单的人变多,而非骑手行驶真正变得安全。
这一现象如何发生?
交安码的变换规则,只是一种定义标示。但在交安码的落地应用上,信息系统生成的问题骑手清单仅由部门负责人提及,实际指导企业的方式尚不明确。
单由《自律公约》来看,颜色仅对入行门槛上有明确影响,即要求新人骑手持"绿码"才能入行。除此以外,政府整体仅透过企业交通安全评级进行监察:交警只会统计平台、站点辖下、当天上路骑手的人均交安码得分,再在日后通报约谈交安等级低的企业。

当天上路的一线驾驶情况与最终等级评定间,相隔巨大的可操作空间,交给了平台自主设计。
于是,平台确实回应了政府要求,骑手确实会因交安名义被封号停单,但停多久、怎么停、何谓"交安",似乎全凭平台定夺。只要骑手单量够大,平台完全可以缩减其停单时间,甚至暂时取消安全规则;同时,当评级只计算当天上路骑手,只需频繁要求低单量骑手维持"绿码",高单量者即可如常赶单。
由此,只有停业者得到安全,只要在路上,骑手的职业内容,就是在危险中极限奔波。

天天这样。就封了一次2小时。 (@是蔡不是菜,发表于2025.07.22)
以美团为例,外卖骑手博主 @老驴记 一则评论交安码的视频下(3),美团骑手 @是蔡不是菜 为了跑单,三天累计已闯过7次红灯,但系统只判定过ta两小时的停止接单。

骑手 @你好啊,宝哥 则指出,美团会人为区分骑手类型,众包骑手和团队骑手的封禁接单时间不同。美团的骑手架构中,团队骑手(专送等)受到更严格管理,通常单量更大、工作时间更长。于是,有众包骑手以"交管部门要求"的名义,一周被封四遍,但"团队(骑手)极个别就封几个小时"。
在评论区,多名骑手带着灰色狗头,支持了这一说法。
爆单没人跑的时候,自然会系统坏了自动解封 (@三十而已,发表于2025.07.12)
在线人多他(系统)正常派单,一旦骑手少他(系统)就开始乱派单,根本不管你逆行还是超时,就是使劲的派 (@凯哥外卖,发表于2025.07.05)
实际上,正如骑手 @猪、八、盖、@三十而已、@凯哥外卖 反映,当骑手较少、系统"爆单"(单量大于骑手承接量),美团会卸下各类限制,一切以完成单量为准,"24小时跑美团都行"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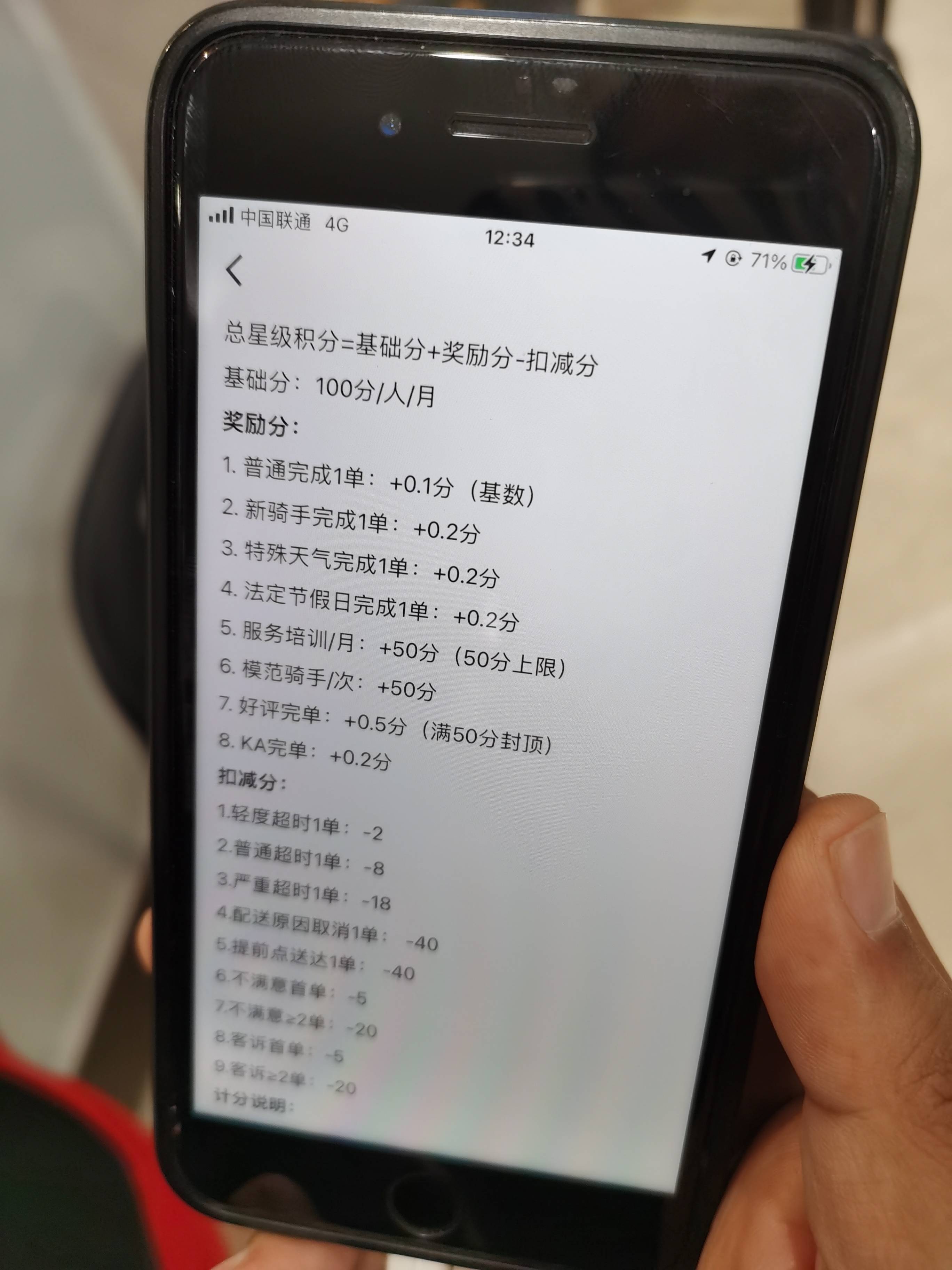
平台企业中的交安措施,并未保障骑手安全,反成了倒逼骑手工作的策略,交安码也是其中一员。
没一方把骑手当人
进一步地,交安码不但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,反而和平台共同形成了更緊迫的骑手困境。骑快了,被交安码罚,骑慢了,被平台罚,加上外卖单价、配送时间都被一再压低的市场趋势,令骑手陷入更艰难的"两头堵"境地。
“大家在现在这种单价想赚到钱,你是不是得多挂单、得速度快?”反问后,@辰巴 没忍住嗤笑一阵,才接着往下,“但它不允许你快,不快你不能多挂单,然后这个单价,你说怎么赚钱?”
@辰巴 是一名外卖骑手,在抖音上感慨交安码推行后, "魔都外卖越来越难跑"(4)。他分享自己一次送餐经历,开的踏板摩托车早在平台上完整备案过,却仍被系统统一视作电动自行车,判为超速,可能会限制接单。 @辰巴 相当沮丧,"越来越难了。"
再度收紧管理的系统,将压力层层叠加到骑手身上。但平台不合理的派单与限时,才是骑手违反交规的根本原因。
骑手 @凯哥外卖 在分享中(5)直指交安码治根不治本,多个骑手都在评论区表示了赞同。
@橘子焦糖玛奇朵 指饿了么给骑手的一分钟实际只有40秒,"跑过的都知道,偷时间";
@三角洲跑刀老鼠🐭 评价平台只是在"既要又要还要",要骑手快、要限时、要顾客体验好,但派单混乱,"反正就是搞骑手呗"。

如果可以选择,没人希望冒着生命危险工作。平台派单的问题根源无人解决,安全配送的薪酬又无法度日,"连个低保都跑不出来(@七天七夜)";但骑手为了生活挺而走险后,迎来的是交安码的再一重罚款,甚至是平台的永久封号,直接失去饭碗。
"要么你赚了钱就交罚款吧,也随时等着封号吧,对吧",@辰巴 在视频最后说道。
"外卖骑手这个工作危险,不应该是我们骑手活该"
除去表面的直接效果,这一系列新的交安措施还有一个隐蔽而深远的后果。它以缺乏充分法律依据的越权做法开了口子,平台因此得以在”合法”外衣下,维持既有的管理框架,继续侵害骑手权益。
"(你说)安全,你应该把所有的人算在一起……为了所有人参与交通当中的一个交通安全,那你应该把所有人都算在内,为什么处罚那些东西,只有美团骑手?"
骑手 @乐吾哦 讲述自己对电子号牌的看法时(6),全程紧皱着眉头。交安码的可操作性,来自政府要求骑手须申领关联身份的特殊电子号牌才能上路,也让后续针对骑手群体的信息收集和交安监测得以实现。但这系列措施的实行,正是将所有人的路面安全责任,指向骑手承担。

南方周末一篇评论文章(7)进一步指出,交安码是"法无授权不可为":政府倡导措施关联就业资格,形成了变相的“从业禁止制度”。 但交通法规中并没有规定的从业禁止,规定交安码的《自律公约》更仅仅是公约,而非法规。措施首先是侵犯了骑手的劳动就业权,更加存在处罚公平的争议。
这种区分由官方完成后,平台企业不仅能化政府措施为己用,更加能打着"交安"的幌子,延续并强化管理逻辑中对骑手权益的侵犯。
如骑手 @༵༺乄 ༿ི༒ྀ༾ 乂༻༵ 的经历,美团的封号方式对骑手展现了一种绝对权力,只需要两行简单"交安"文字,赖以为生的帐号随时可能被封禁,骑手只能对不透明的规则认命。
又如美团的"安全分"制度,要求骑手配送开启前置摄像头,全程摄像识别骑手的行动,不开启时将被限制接单。这一操作是否在隐私权上越界?美团是否留存影像,将作何用,骑手本人又是否知悉?
经过官方推行的电子号牌和交安码后,这些权力不对等,更加无人追问。

@乐吾哦 的分享视频长达半小时,大半时间是镜头正对脸的清谈,穿亮黄色上衣,系戴同色的骑行头盔。不过,在视频开头,他先拍了一条完全的楼梯,再转到一条满布碎石的泥坡路。它们都被美团的骑手导航划作"应行驶道路",但骑手给美团的反馈再无下文。
"我真的要为我们骑手这个职业说明一下,我们很危险,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活该……说实话啊,我确实是有点害怕。骑手这个工作很危险,那是骑手活该,我很害怕这样的事情,会成为社会的一个常识。"@乐吾哦 皱着眉说。

部分参考来源
(1)上海首创外卖骑手“交通安全码”:安全守法的“绿码”骑手才能接单 https://www.jfdaily.com/staticsg/res/html/web/newsDetail.html?id=940188&v=1.7&sid=67
(2)随申办APP内,由“上海交警”页面的快递、外卖服务查询入口,可查看《自律公约》全文
(3)【老驴记的作品】上海多名骑手封号,只因为交通安全码上线,交罚款可以... https://www.douyin.com/video/7525775774185442595
(4)【辰巴的作品】魔都外卖真的越来越难跑 https://www.douyin.com/video/7529747942711299385
(5)【凯哥外卖的图文作品】最近上海不是在进行绿黄红码吗?说句真心话,这就是针... https://www.douyin.com/note/7523600391238978862
(6)【乐吾哦的作品】视频很长中间可能也有点乱,各位将就一下。外卖骑手这... https://www.douyin.com/video/7526888859352386879
(7)“红码”骑手列入行业“禁限名单”?良法美意也要程序正义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F3aekZqfz_jepKCI3FqmQ
工人有事,我们报道
我们收集一线工人的声音,呈现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劳动者生活;我们探究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体制、剥削逻辑,力求呈现劳动者的处境,看见来自工人的行动和抵抗。快手、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体是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。采访劳动者、与工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我们希望通过文章和报道的连接,能使所有劳动者团结为一张巨网。我们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,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。工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,工人的声音最有力量!
劳动者筑起一砖一瓦,在一条条产线上铸造中国制造的奇迹。劳动本应该被尊重,现实中,劳动者被剥削、被边缘化,主流话语一边将劳动者塑造为卑微、值得同情的受害者,一边忽视、贬抑、打压劳动者的行动。我们希望在劳动者的世界中,重新看见劳动的价值,重建劳动者的尊严。
征集伙伴
如果你也对工人议题、劳动报道或工人运动有兴趣,想参与工事有料,欢迎直接写信联系我们: [email protected] !
加入我们的社交媒体: Twitter | Instagram | Telegram





